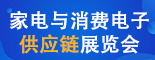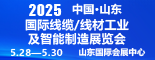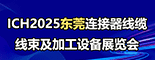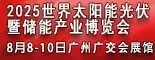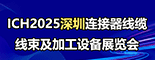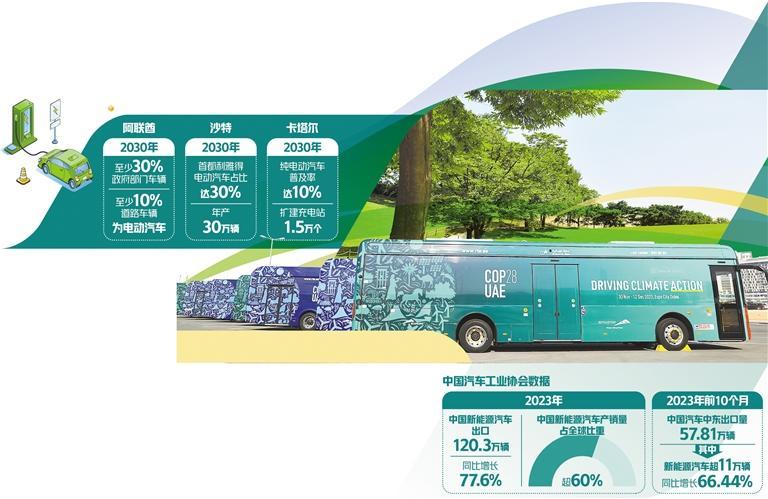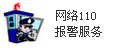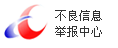通过改革开放,我国形成了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这种模式并非一成不变,而要根据国情变化不断调整和创新,在应变中不断完善和发展。
当前,资源与环境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中必须要面对的关键问题,迫使社会转型向环境友好型与节约型社会看齐。同时,经济重心逐渐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过渡转移,第三产业的增加占比总体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从电力消费结构来看,尽管第二产业的电力需求仍然占较大比重,但从近几年的趋势看,第二产业的电力需求占比在逐渐下降,而第三产业电力需求量占比正逐步提高,而这与经济重心的转移是匹配的。从二产内部看,钢铁、水泥等高耗能行业产能已经饱和或达峰,而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新兴产业等是二产的新增长点。就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的趋势来看,研判未来二产电力强度呈加速下降趋势,而三产电力强度则受交通电气化和办公自动化的发展呈降速上升趋势。
截至目前,我国用电负荷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及珠三角地区。从用电结构来看,工业用电量占比从1990年的78.22%下降至2012年的72.81%,生活用电占比从1990年的7.72%上升至2012年的12.50%。从生活用电情况来看,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人均生活用电达到700kWh左右;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人均生活用电量已达790kWh以上。2000年至2013年间,全国居民生活用电量维持年均增速10%左右,北京、广东等发达地区人均生活用电量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增速相对缓慢。未来10至15年是我国完成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跨越的关键阶段,根据北京、广东、上海的经验,此阶段居民用电增速有显著放缓的趋势。
综合上述分析,“十三五”电力需求将步入中速增长期,年均4%左右;2020年后会进一步降速到3%以内;2030年后将进入1%左右的饱和低速增长阶段。
电力规划思路必须调整
一直以来,电力部门主要通过单纯增加发电装机容量满足日益增长的用电需求,这种发展模式急需调整。
第一,节能是最重要的能源资源,欧美国家已普遍实现电力能效每年节节电1%以上的目标。而我国一方面在规划层面上未将能效作为重要资源纳入规划,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电源的快速扩张;另一方面,能效政策实施力度也显著不足。当前,电网公司每年完成上年电量和最大负荷0.3%的节电目标,与欧美发达国家相去甚远。因此,“十三五”期间,应把大力落实能效政策作为优化电力行业发展的重要措施。首先,电力规划应以“节能优先”为原则,把能效资源纳入电力综合资源战略规划。其次,如果实际电力需求增速超出预期,可在能效领域挖掘潜力,最终达到能效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0.6%—1%的目标。
其次,以煤电为主的规划思路需要根本性的调整。燃煤发电在我国始终占据着绝对优势,不仅是因为资源禀赋带来的经济成本优势,还因燃煤发电机组具有稳定可控的出力特征。不可否认,作为主力电源,煤电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巨大,而当前环境代价日益凸显,温室气体峰值约束日益强化,而可再生电力、气电的经济性有望大幅改善,有必要从根本上调整各类电源的定位,特别是要在新增电源中优先发展清洁能源,煤电的位置应由一直以来的“主力”调整为“补充”。
最后,尽管国家政策不断向清洁能源倾斜,但弃风、弃水、弃光等问题仍十分突出。2014年并网风电平均利用小时1905小时,同比减少120小时。吉林和甘肃风电平均利用小时数低于1600小时,均亏损运行。2015年,电力需求进一步放缓,预计弃能源问题会更加严峻。综合分析,背后主要是体制机制问题。从电力规划的角度来看,下列问题必须深刻反思和解决:首先,规划是政府主导还是需求驱动与政府引导相结合?其次,电源规划与电网规划如何统筹协调,大型可再生能源基地规划如何与电网规划及市场需求配置对接,配电网规划如何与可再生能源分布式消纳无缝衔接?再次,为适应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并网的要求,供应侧与需求侧如何组合,来满足电力系统可靠性与灵活性的要求?最后,规划由谁编制,按照什么程序编制,执行的过程中如何根据实际动态调整?“十二五”期间我国未出台统一的电力行业规划,2014年更是把电力项目审批权限下放地方,电源与电网各自为政、电源规划不考虑系统性、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等现象,都是当前电力规划体制机制的突出问题。
“红线”约束下的煤电清洁高效发展
资源禀赋造就了我国电力行业“以煤为主”的现状,即便调整煤电在新增电源中的定位,其优势地位仍会继续保持。
“十二五”期间,GDP增速逐年放缓,从2011年的9.48%下降到7.4%。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电力需求也随之告别高速增长时代,但是电力规划未及时调整,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很可能会出现煤电大规模过剩的局面。
新形势下,继续大规模新建煤电后患很大:其一,大规模新建煤电基地与2020年15%非化石能源占比目标是相悖的;其二,近年煤电的利用小时数一直处于下降通道,2014年火电利用小时数4700左右,从2015年前半年的数据来看,今年火电利用小时数可能降到4500,大规模新建煤电机组必然导致运行效率进一步恶化;其三,为完成2030年20%非化石能源比例目标,2020年后低碳发展的要求会更高,“十三五”期间继续大力发展煤电会大幅增加电力低碳转型成本。如果现在不加约束,2020年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要求可能会导致新一轮的煤电机组大规模关停,将造成更大的资源浪费。
此外,煤电发展还面临着“红线约束”。首当其冲是大气污染,煤炭燃烧所产生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及粉尘等污染物均是雾霾形成的重要因素,而电力作为用煤大户,从环保角度必然会受到制约。其次,我国新建煤电机组多规划在大型煤电基地,均处于水资源严重匮乏地区。最后,即便实现超低排放,温室气体峰值约束也难以跨越。尽管可以利用碳捕获与封存来降低排放,但是经济代价和风险都过高。
电能替代对治霾和能源系统优化有着重要作用,但并不能以此为由继续大规模发展煤电。实现2020年的非化石能源目标,在中速电力需求增长预期下,煤电有望在2020年达到9.7亿千瓦,接近峰值,届时电力总装机规模为19.2亿千瓦。而且,这一结论是建立在每年实现600亿千瓦时电能替代能力的基础之上。通过实施电能替代,到2020年电力部门可增加1亿吨标煤的供应能力,对应煤电规模约需增加5000万千瓦。也就是说,实施电能替代已经对煤电规模形成了较大的预增空间。但最终,以煤电替代其它高污染、低效率的煤炭利用形式,只能解决环境问题,不能解决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电能替代的根本之道是可再生能源替代。